前不久读过野夫(郑世平)的《乡关何处》,该作犹如乡愁诗文中的一曲《琵琶行》,低眉信手续续弹,弦弦掩抑声声思。由于年代久远,未曾经历,只能从那些特殊的符号中收获血脉喷张与精神洗礼的感时伤怀。
而今拜读王开岭的《每个故乡都在消逝》,沉浸在一种深深的怀旧情结中。有时候,真害怕听到“日新月异”这个词。你曾经熟悉的地方,几个月后再去,或者几周,有时几天,可能已经面目全非了。你对这空间的消失毫无心理准备,待要细细回味以前在这里的生活,几无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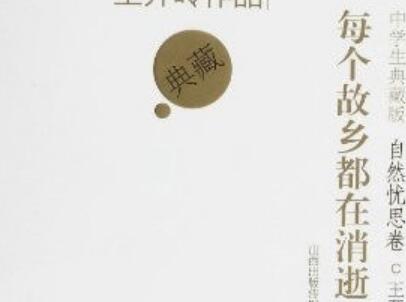
这何尝只是王开岭,是我,少数几个人的乡愁呢?我现在居住的地方,我不知道它的前世,但从小区周围还残留的菜地,我可以猜测这里其实也是他人的故乡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开岭用上了“每个”。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的故乡在沦陷,在消逝,在被他乡人占据,我们自己,却又在别人的故乡上,毫无知觉地侵入。
幸运的是,我们这辈人多少还留有一些故乡的记忆,而我们的孩子们,他们的乡土在哪里?他们住在被围墙、防盗窗包围的水泥囚室里,没有说共同方言一起长大的伙伴,没有“看着自己长大”的那么亲切的长辈街坊邻居。所以我理解他们的孤独,他们看电视,玩电脑游戏,说到底,其实只不过是在转移这童年的孤独。
王开岭的《每个故乡都在消逝》里有一段话:“我们唱了一路的歌,却发现无词、无曲;我们走了很远很远,却忘了为何出发。”似乎与大师丰子恺的漫画异曲同工。
王开岭被称为中国青年思想家三架马车之一。他是个用心灵说话的人。就像一个孩子,凭愿望突然指认感兴趣的东西,且懒得滞留,懒得炫耀,抛出最重要的发现后就迅速跑向下一站,不贪功,不居奇……他说一个人要努力还原真实,还原自我和世界的真实,要做一个精神正常和精神明亮的人,而不要追求非常态、非本能的唯美与深刻。
每个故乡都在消逝,消逝的不只在王开岭的文字里,不只在丰子恺的漫画中。在常态的消逝中,我们能做些什么?也许我们还能从这些符号和勾画中找寻恍惚的记忆,从邓丽君的音韵中回响曾经的故事,可我们的孩子仅剩下只有与时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