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肝游戏拖了几天。重要,但真的读起来非常无聊。正文大概560页,前309页都是“准备性工作”,非专业读者建议只看309页以后。先说缺陷。最大的缺陷就是作者一方面说爵不是虚名,关系到直接的身份性利益,但直到最后作者也没有找到除了犯罪可以减刑以外任何一条由爵所带来的身份性利益,只是在乡党之中更受人尊敬恐怕不符合作者声明要找到的东西。再说重要的成果。
第一个。作者指出的增渊龙夫任侠研究的缺陷,是妥当的。任侠关系的特点是在地性,个人性,易封闭性,无力作为整个秦汉帝国秩序形成的“内面支撑”。增渊龙夫指出的郎官与皇帝的类任侠关系,所显示的只是皇帝与官僚系统之关系中的两面性:一方面官僚系统的政策方向乃由皇帝所给予,另一方面官僚系统作为平衡性的公权力机构,会排斥皇帝的某些意图。皇帝需要培养一个与自己紧密相连的近臣集团,以便让他们承担如皇帝使者,法官,关键地方官等节点性的职务,让他们为贯彻皇帝意图而出力。
它无法解释整个官僚系统的运作,更不可能解释帝国秩序如何形成。毋宁说,增渊龙夫和西嶋定生的研究是互补的。爵制塑造的他律性秩序和任侠关系的自律性秩序,在地方上,二者处于一种竞争与合作兼有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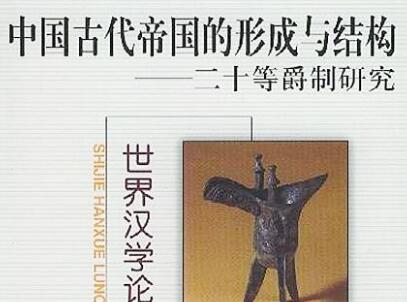
国家想将地方导入爵制秩序,地方性的任侠小集团时常会表现出抵抗,但有时也表现出一致,后者往往显示出中央政治力量的衰退,难以贯彻目的性强的政策,退居平衡社会力量的仲裁者地位,例如后汉。但放眼整个帝国,任侠关系不能承担塑造整体秩序的任务,必然要求一种总体性的政治纽带(同时显示出一种意识形态特征),在这点上,须得承认西嶋定生说的才是对的。
第二个。作者在序章梳理了中国学者对秦汉社会形态的争论,但结尾并未以自己的结论做出回应。如果接受作者的研究结论,那么秦汉是“封建社会”或者“奴隶社会”的说法均告破产。作者已经谈到的是,秦汉自耕小农的数量远远多于耕种豪族土地的佃农,斤斤计较数量上远远不是主要部分的佃农是封建农奴还是奴隶是可笑的行为。要回答秦汉的社会形态是什么(如果非要给出一个总概括的话),当头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自耕农地位的性质。
中国学界所谓秦汉是奴隶社会的说法是从秦汉有大量的奴而来,但首先,有数量庞大的奴并不承担生产任务(常识,不解释),其次,刨除这一部分,剩下的奴的数量无论如何相较自耕农不占数量优势。那么一个主要的生产任务并不由奴隶承担的社会,能叫“奴隶社会”吗?更何况,“奴婢”是不是奴隶这点本身仍是一个问题。马克思本人提出的总体奴隶制,作者已在书中指出不能用来理解秦汉社会。秦汉社会不是封建社会,从作者的研究来看也是显而易见的。
如作者所言,封建社会的特点是统治者与农奴以土地为纽带结合在一起,还可以补充一点,二者关系的内核是经济强制,但在封建社会中又表现为政治强制(统治/被统治),用马克思的术语说,二者的关系是“超经济强制”的。但秦汉社会中,首先,即便将整个官僚系统再加上皇帝都视为统治者,也不存在统治者一定是封建地主的社会规律,换言之,封建社会典型的普遍性“超经济强制”关系在秦汉社会中是找不到的。
其次,至少在观念和名义上,只有皇帝是统治者,官僚不是统治者(如“首先”中所言,有时官僚在实际上也不完全符合封建社会中的“统治者”身份),要探查生产者与统治者如何结合在一起,也应该以皇帝和编户齐民如何结合为对象,作文www.yuananren.com作者所得的结论是:皇帝通过爵制与编户齐民形成了一种拟制性的直接人身结合,并不以土地为媒介。
再次,作者正确地指出秦汉的“赋”也不是封建地租,而是源于周代有爵者对天子的义务性军事负担,因为民被普遍赐爵,因此这种军事负担的征收也因之成为普遍的,书中考察赐爵的下限,找到了七岁已被赐爵的证据,那么很有可能,汉代的民爵赐予资格从征收口赋的三岁起就有了。这里或可再补充一点:承接以上结论,那么至少在观念和名义上,编户齐民既是生产者,也有相当于“骑士”的身份,要缴纳军事贡品还要服兵役(尽管实际上远远不能与“骑士”相比拟),当然不能再理解为封建农奴,也不能理解为奴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