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89之前并不存在民族意识的世界中,帝国的对应物是城邦或者王国,因此,帝国一方面在世俗意义上宣称自己能够造就持久的和平,另一方面则利用宗教协和赋予自家某些神圣的使命。作为从城邦共和发展起来的帝国,罗马在奥古斯都之后的三个世纪中企图用“文明开化”作为自家的使命,但当这种教化趋于内卷时,就不得不用一种新的宗教来完成凝聚力的转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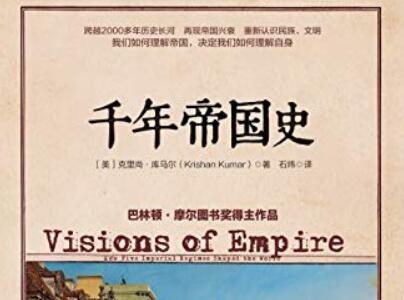
中东和东亚的帝国同样重复了这个过程,在交流较为频繁的中东,帝国的稳定性受到四面八方威胁的影响,因而更加强调自己在宗教上的独特性,借以团结境内臣民。而在较为孤立的东亚,中央帝国则通过扶持儒教,获得了类似罗马帝国早期的存在基础。而更为封闭的地理环境,也让这片区域维持一个连续性迭代的帝国变成了可能。
1789之后,帝国的存在发生嬗变,在nacionalismo的冲击下,旧有的,用宗教或者正统性作为团结的路上帝国(奥地利、俄国、奥斯曼)愈发摇摇欲坠,传统的帝国君主不能再用神圣的字眼让领土内的居民心悦诚服。为此,大部分陆上帝国也就不得不走上了和民族主义媾和的道路,看在一战之中被撞的粉身碎骨(哈不斯堡是个特例,它在19世纪中期被普鲁士击败后,被迫放弃了对德意志认同的尊崇)
取而代之的则是从邦国发展起来的海外殖民帝国。然而无论是英国还是葡萄牙,在对海外领土进行统治时,仍然使用到了大量古代帝国的传统法术(包括强调帝国的一视同仁,和平的珍贵,对当地土豪的拉拢,以及对当地族群认同的淡化和压制)。从这一点上来看,帝国的延续性又是及其延绵流长的了。
《《千年帝国史》读后感600字》.doc
将本文下载保存,方便收藏和打印
导出文档
复制全文
导出文档
